nga人口普查,大家谈谈对客家人的看法?
nga人口普查,大家谈谈对客家人的看法?
客家人,这是一个充满颠沛流离、饱经风霜的苦难的代名词,客家人迁徙过程充满血泪和辛酸,自五胡乱华以来,大批中原人举族南迁至长江流域,西晋王朝灭亡后,中原成了胡人的天下,野蛮的胡人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他们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又以赣江、汀江、梅江流域为大本营,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这时,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这是客家人第一次大迁徙,其后有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变、蒙元入侵、满清入主、康熙的复界令等多次迁徙。 中原文明的圣火,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四处点燃;在漂泊苦难中熊熊燃烧,客家人背负中原文明辗转南迁,使古老的文明得以维系与延续,客家人是华夏文明古老的负载者,客家话(包括广府语、闽南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南宋庆元间任汀州教授的陈一新的《跋赡学田碑》有云:“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这说明自中原地区给金人入侵后语言已受到了影响,唐代诗人胡曾早年一直居住在长安,因为他的胡人老婆总说蹩足汉语有一天而诗兴大发,诗曰 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 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 而胡曾的这首《戏妻族语不正》,讲北方话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此诗,在北方话中,十石,真针,阴因都同音,而唐朝时的正音,针、因是m 尾,真、阴是 n 尾。十、石都是入声,但十是辑韵(p尾),十是 陌韵(k 尾)。可见当时胡曾的妻族已经把m尾的鼻音和 n 尾的鼻音混同了。如果用客家话、广府语、闽南语来读,那就大不一样了。北宋靖康之变之前的“我”一直读ngai音,在客家话完整保存了下来。现在北方很多地方声母仍读作ng,“俺”本来是“我”字的衍生,读ngan,在老派山东话里还是这个音,后来因为普通话里没有ng声母,变成了an,当然,普通话中也有跟客家话发音一样的,譬如:“东西”。明代《永乐大典》引宋代某氏《漫游集》《过汀州》诗一首:“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说明宋代汀州地区的语言方音接近当时的北方古汉语而异于闽语。 明代《永乐大典》引宋代《图经志》曰:“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之人同等”。说明当时潮州与梅州都有各自的土音,彼此不相同。而梅潮之间所操土音则与梅同。宋代潮梅之间相当于今天的大埔丰顺等地,皆是操客家话的地区。这揭示当时方言分布于今天大体相同。可推断早在宋代客家方言已经形成。 百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至今尚没有完全弄清楚,不过以“百”字来推断很可能是南方多种多样人群的总称——正如今天的北方人会把广东那几种相差很大的方言都归为“鸟语”一样,先秦的华夏人约莫也是没有太大的兴趣专门研究当时南方的人群到底如何分类,而是用“百越”大而化之地概括了。彼时不单广东,整个南方都是百越的天下。 古百越人的语言并没有留下太多记录,《越人歌》是少数记载古百越语的珍贵材料之一,据说是越人船夫对楚国令尹鄂君子皙的吟唱,原文是:“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虽然这越人唱的到底是什么语言尚存在争议,目前就有古越南语、古侗台语(现代泰语、壮语的祖先)乃至古苗语等等说法,不过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看得出来绝对不可能是汉语。长江流域尚且如此,本是中原人眼中化外之地的岭南就更不用提了。 秦灭六国以后,继续将扩张的目光投向了岭南。随着秦王朝三次攻打百越,岭南终于被纳入中原政权治下,秦在今天的广东设置了南海郡,参与平定岭南的将士在岭南定居,将汉语带入了广东。随着中原王朝对岭南控制力的不断增强,加上南迁移民,广东地区逐渐转变为汉语占优势的地区。其中珠江三角洲一带,以广州为中心的汉语慢慢发展成一支别具特色的方言,即为粤(广府)语,而客家话顾名思义,即(远方来的客人)客家人说的方言。虽说有人认为客家人的南迁史可以追溯到东晋,但是就地方志书来看,客家人迁入岭南的时间比广府人和潮汕人都要晚。当时广东各地肥沃的平原地区已经基本开发完毕,所以客家人往往聚居在开发不易的山区,如兴宁、梅州等地。宋初《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兴梅地区仍以畲瑶为主,梅州客家不过300余户,潮州更是没有客户。而过了一百年不到,《元丰九域志》中客家人在兴梅地区已经成功“反客为主”。 客家人口的逐渐增加使得山区承载人口能力低下的劣势开始凸显。于是客家人向珠江三角洲迁徙,并再次改变了广东的语言分布。例如明嘉靖年间的《广东通志》尚且记载“若夫博罗、河源近于(惠州)府,则语音相同”,表明当年两地并不说客家话,但是随着客家人的逐渐进入,博罗和河源现今都是以客家话为主了。随着客家人逐步深入粤(广府)语区,粤客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渐渐增加,客家人农耕技术远比“土人”(广府)先进,且素以吃苦耐劳著称,但毕竟是后来者,当地又是平地少、山地多的贫瘠所在,肥沃宜耕的平地基本被“土人”(广府)占据殆尽,客家人只能跑进人烟罕至、荆棘丛生的深山,然而随着一些客家名门望族购买广府人的田地,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田地落入客家人手中,“土人”(广府)开始不满,认为是客家占地主“鸠占鹊巢”以至引发后来的土客械斗。无论是说粤语的广府人还是说客家话的客家人,却对自号广东土著没有太大兴趣,而是想方设法把自己说成是“中原贵胄”的后代,对方则是当地蛮夷,如顺德人黄节编写的《广东乡土历史》里就说客家人“非粤种,亦非汉种”。 在这种背景下,粤语和客家话也纷纷被当作是正统的象征和证据。广府方面,陈第的《广州音说》声言:“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至广中人声音之所以善者,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如此也。”一下把粤语拔高至隋唐时中原音的地位。反过来,客家话则“硬直”、“入耳吵吵”。 当然,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抹黑,客家也不甘示弱。如客家人徐旭曾的《丰湖杂记》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记载:“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之风俗语言,至今犹未能强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彼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阅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客家话既然“甚正”,也无怪乎客家人要“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了。 虽然早期南下的汉语是顺利地把当地的百越语言“强而同之”了,但是到了客家南迁的时候,广府人在珠江三角洲已经站稳脚跟,并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强而同之”显然是不太可能了。 随着广东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客之间因生存竞争而产生的对立情绪也不断滋生,加之清廷从中挑拨,甚至引发了大规模械斗。譬如今天的四邑地区(珠江三角洲西岸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合称四邑),土客械斗尤其惨烈。据载“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万众”。 长期的大规模械斗对客家人的损伤远远超过广府人。虽然客勇善战,但是珠江三角洲毕竟是广府的大本营,广府人在械斗失败逃亡的情况下一般多少都有些亲朋好友可以投靠。相较而言,客家人要是被迫离开家园,往往就无处可去,沦为盗匪,变成了官军清剿的对象。 最终清廷为了解决土客械斗问题,将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客家人遣散回粤东客家原乡乃至外省,今天赣南地区的客家人不少祖先就是土客械斗以后从广东迁入江西的。这一系列变故导致珠江三角洲地区客家人口锐减,如四邑土客械斗前客家人可占当地总人口约五分之一,而械斗尘埃落定后只为百分之三。客家在珠江三角洲的势力大大缩减,客家话因此也失去了在珠江三角洲进一步扩张的可能。 土客械斗一直影响到解放前,据说当时双方互不通婚,互不来往,各个村庄有围墙、雕楼,有人把守,如有外人进入放枪便打。所以广东很多地区都保存有完好的围屋、围村、雕楼等,现在已成为历史文化建筑受到保护。
如何看待胡人汉化南下的客家人群体?
我看了下大家的回答,大都是人云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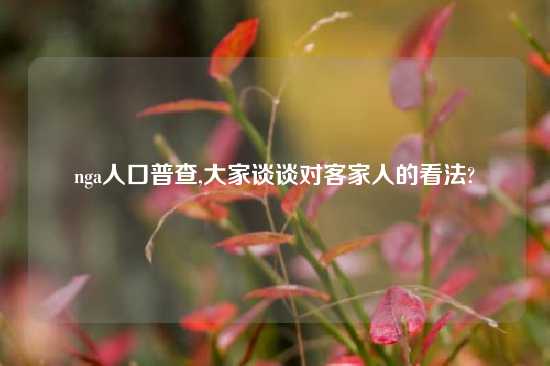
关于客家之说,早有定论。是宋时的籍贯制度的产物,在人口造册上,对于类似今天流动人口的称呼“客居”(是相对于不流动稳定固有的主居的叫法),民间老百性叫客家,久而久之传到现在就叫客家人了。
而此产物为何南方有保留呢?
因为南宋疆土都在现在的客家人主居区,而此时北方甚至中原已不是汉人天下,故北方鲜有客家。
至于用”胡人南下为客家“这种命题显然是居心叵测。而看客们往往爱凑这种热闹,所以命题者抑或是哗众取宠。
客家人不是个民族,只是籍贯制度对移居家庭的称呼,所以把客家定位为纯正中原原汉人似乎有些不妥,这与命题恰恰是两个极端。话说回来,已汉化的胡人后裔有没有也随潮流南下的,不能肯定,但显然更不能否定。也就是说有这种可能。由此得出客家人的成分绝非传说那样单纯。
既便如此,用”胡人南下为客家”命题投放《头条》实在欠妥。这就不仅仅是故弄玄虚卖弄学问、哗众取宠了!乃颇具不良用心…
为什么WOW里面联盟和部落仇恨这么大?
难道没有看到问题本质吗,从剧情上来说部落与联盟多次冲突,这要追究起来(剧情和玩家)恐怕要比魔兽小说还要厚,虽然部落对于联盟来说是“外来者”,但部落更可怜自己的家园惨遭毁灭,它们本身从最初就是对立面,但多次合作把真正的“外来者”赶跑已经互相认可了对方。
从玩家角度来说很多人都知道“部落猪”和“联盟狗”这个词,这是小说里对立阵营加大激化矛盾的一种方式。真正的WOWER都知道“部落猪”和“联盟狗”更多是褒义的,每年春节玩家都会开小号去对立阵营说一句:“部落猪新年快乐”、“联盟狗你好 新年快乐”。
“部落猪”更多的是形容兽人高大粗壮的体型,“联盟狗”则是表达联盟内部黑暗迂腐的称谓。没有语言出现的感人事件已经不少了。
现在的新玩家可能忍受不了游戏环境,被杀的不能自理会去对立阵营辱骂,包括小号被杀那种火大的心情。我的看法就是现版本游戏趋于快餐化,玩家会为了装备装等疲于奔命,没有停下来享受游戏的乐趣,《魔兽世界》开始“固化”了。
对比一些粗制滥造的游戏,《魔兽世界》里的仇恨有很多感情成分,剧情的潜台词也一直再说:“放下仇恨”。而其他游戏内仇恨(包括玩家之间)那是实实在在的“仇恨”。
@游戏没有圈儿 专注闲暇时间在悟空问答混日子 我的回答有帮助请点赞或关注。
赣语和哪种语言接近?
客家话。
赣语和客家话在语音上是汉语七大方言中最为接近的。一方面,江西境内赣语和客家话的分界线一直模糊(比如赣语也有人把“我”读成ngai或nga的),但是词汇上差异较大,且心理上互不认同,所以是否应该合并为同一种方言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赣语居民(江右人)和客家人一样,都是始于五华乱华之后南迁的北方汉人之后,这部分人取代了江西原本的古楚语和古吴越语形成了古赣语。后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大约于宋末元初时开始分道扬镳,一部分继续迁徙保留了更多古赣语的特征成为后来的客家人,而一部分则留了下来并与后来的北方移民融合并受周边方言(主要是吴语和湘语)影响形成了现代赣语(明代基本成熟)。
江右(说赣语的)和客家虽为两个不同的民系,但是我们对于客家人都有种莫名的亲切感,特别是听到客家话的时候,祝愿客家兄弟繁荣昌盛!客赣一家亲!
安徽省内哪个地方的方言最难听懂?
安徽的方言难听懂程度,是由北向南递增的。
皖北的中原官话是安徽省内五大方言中最接近普通话的方言,但和普通话也有明显的差别。
除了音调上的差异外,还有就是区分尖团音、声母sh的合口字大都会读成f(水=fei、书=fu)、平卷舌属于中原官话的洛阳型:有些卷舌音的声母会读成平舌音(茶=ca、沙=sa)。
其中信蚌片中有的声母h、f不分,后鼻音韵母eng、ing的字一律读成前鼻音en、in。
皖北方言中出镜率最高的应该就是“管”了,就如同河南话中的“中”。
江淮之间的江淮官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下的淮西话。
对比普通话,江淮官话声母n、l不分,统一读l。ing、eng全部读成in、eng。有一个喉塞音-ʔ入声尾韵。
长江南岸的江淮官话不区分平卷舌,ang/an不区分。旧巢湖地区和安庆的江淮官话有ng声母。
大部分地区虽然分平卷舌,但是平舌音z、c、s,卷舌音zh、ch、sh和舌面音j、q、x使用时非常混乱。最经典的就是合肥话中的“洗”,普通话拼音是“xi”,在合肥话中读“si”。(关于那个“你先死,你死完了我再死”的段子,有兴趣的可以自行百度。)
江淮官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咸山摄三分,这也是造成了和普通话差异较大。普通话中咸、山两摄已经合流,韵母只有一个an(包括uan、ian)。
举个简单的例子(合肥小片):在普通话中“办”和“半”的读音都是ban,合肥话中“办”读ban,“半”读bong(半个=bong guo)。
“环”“欢”普通话中为“huan”,合肥话中“环”读“huan”,“欢”读“huong”(欢喜=huong si)。不同地域有差异。
声调比普通话多一个入声,庐江话多一个声调,入声调分阴入和阳入。
皖西南是赣语怀岳片
见母无颚化,即普通话中的j、q、x全读成g、k、h。如:家(ga)、敲(kao)下(ha).
中古汉语的疑母、影母在普通话中合流为零声母,但当地方言中分成前鼻音声母n,后鼻音ng和零声母。如:艺(ni)、我(ngo)、吴(wu)。有些地方声母“l”被转化成“d”,比如:家里(ga di)。
韵母“u”丢失,uo变成u(罗:lo),un变成en(村:cen),uan变成on(端:don),单韵母“u”又变成了“ou”(杜:dou)。
有喉塞音入声韵尾,部分地区有“l”“h”入声韵尾。
接近江淮方言区的地方受江淮官话影响,声母“n、l”不分;无后鼻音韵母“eng”“ing”,归入“en”“in”。
声调有六个,不同地区调类有差异。
皖东南的吴语区更难些,保留中古汉语的全浊声母,与全清、次清(送气音)声母三分天下,铜陵至宣城一带的吴语区全浊声母又分化出强和弱两种送气音,又多了几个声母出来。一下子比普通话多出10几个声母。
咸山摄二分,臻深曾梗四摄舒声字合并。
不用多说,汉字的数量就那么多,这两个变化会多出不知多少个读音来了。可见得到有多难了,好在宣州片只有5个声调。
皖南徽语方言原本是吴语的徽严片,后来独立了。和吴语一样很混乱,虽然没有全浊声母,但塞音和塞擦音大多数发送气音,如:“白”声母是p;卷舌音声母有的读舌面音的,如:“张”读jio;有的读平舌音的,如:“沙”读so;有的舌面音有不颚化了,如:“甲”读ga。零声母又变化为“ng[ŋ]”“gn[ɳ]”混用,如:“矮”读nga,“狱”读gniu。韵母的差异就更大,总之对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不亚于外语了。
上面这些只是列举的小部分,总体来说安徽省内方言越往南越难懂。
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量移民填充皖南。
河南移民带去中原官话、湖北移民带去西南官话,浙江移民带去了南部吴语和闽南话,福建移民带去了闽北话和客家话,江北移民带去了江北的江淮官话,还有畲族的畲话。
这么多方言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可见皖南的方言是多么复杂了,即使村与村之间语言不互通也是正常的。






